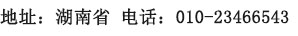那年夏天,四川作家周克芹突然英年早逝。我虽然是四川人,但却以贵州人自居,在四川作家中,只有周克芹能算是有些私交,比如路过成都可以到他家坐一坐,聊聊文学,有时甚至还可以留在他家里吃点便饭。于是我决定以记者身份去采写一篇报道,也算是尽一份朋友的悼念之情。
“遥远的在山那边”——据说这是一行最美的英诗,我深以为然。我从小就受着这种“山那边”的诱惑,才从大娄山中如梦似幻地奋斗到北京。周克芹的命运也符合这行英诗的逻辑:一个简阳红塔乡的农民,穷得连老婆生孩子都要背门板去卖,却也是受着“山那边”的文学梦牵引,才一步一步成为中国名重一时的作家。
命运之所以似幻如迷,就是因为其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周克芹的家乡葫芦坝,由三个葫芦一样的田坝组成,竹林掩映着日子艰辛的农家。当地农民把干农活称为“背太阳”,如果说别人白天“背太阳”,晚上还要写小说的周克芹,则是“太阳月亮一起背”;然而,就像太阳曾经照耀过周克芹家乡一样,周克芹也敏锐地捕捉到了碾压自己家乡的时代轨迹:他写故乡葫芦坝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终于一鸣惊人,被拍成电视剧,被改编成川剧,还被北京两大电影制片厂同时改编成电影,最终获得标志中国长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茅盾文学奖”。
然而,四川已无周克芹。
从简阳红塔乡往南几百公里,一直走到川黔边境的大娄山中,就到了我的故乡。
我的童年充满一种“五分钱的浪漫”。我不记得自己第一次是怎样捡到五分钱的,反正,无论多么严谨的大人,都会在无意间遗落一些硬币;或许,有些硬币本身就像精灵一样,总想从大人的口袋里跳出来,滚落进草丛中,去制造一种“五分钱的浪漫”。头天掉落在路边草丛里的硬币,在第二天太阳重新升起时,便会和草丛中的露珠一起闪闪发光,向从它们身边走过的孩子发出亲切的召唤。我就曾经这样喜出望外地在草丛中扒拉过硬币:看着硬币上具有质感的阳光,嗅着它夹带的野草清香,一种“山那边”的冲动就从我心底产生出来。——正是这种意外的诱惑,使我对生活始终充满幻想。
在我童年的大娄山中,五分钱是能派上一些正经用场的:可以买两支铅笔,也可以买一个简易的削笔刀;或者是去买一个米粑,喝两碗豆浆;如果等到赶场天,还能从农民的背篓里,买半碗红得像炭火的杨梅,或者一碗堆得溜尖的李子。
那一年我“家庭成份”不好,在四川上不了高中,母亲坚持送我去贵州读。故乡同学都嘲笑我为“贵大”,因为那个年头实行工农兵学员,靠的是推荐。有些同学的家长干脆让孩子初中毕业就“上山下乡”,然后等着推荐工农兵学员,至少推荐出来工作;但我母亲却以她的人生见识坚持让我读书,这在我们也算是一种“无望之望”吧?结果,在整个时代招生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我正好赶上高中毕业,成为故乡学校里唯一上了大学的孩子。
如果人生失去幻想,故乡孩子将会怎样?
我认为还有一行最美的英诗,那就是西方“圣诞童话”中的那种浪漫诗意:孩子们在临睡之前,纷纷把自己的小帽子和小袜子挂在床头,因为他们相信,即使是大雪纷飞的深夜,圣诞老人也会从北极滑着雪撬,给他们送来礼物。
公路仍然在简阳红塔乡延伸,铁线草贴着公路延伸,夏日的阳光,照着公路和公路两边的铁线草,幻想和幽默像清风一样拂面而来。——我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硬币,当然已经是五毛或者一块的了,我手一挥,就把它们撒进了公路旁的铁线草丛中;我幻想着一个小小的童话能够在铁线草丛中诞生:我希望某天早晨,铁线草上阳光灿烂,硬币也闪烁着光芒的时候,能有上学路过这里的孩子,逐一从铁线草丛中拾起这些硬币。——这些包含着惊喜的硬币,虽然微不足道,但却能在孩子心中激起一种“山那边”的幻想。
从四川简阳采访回来,完成报道任务后,我就决定写这样一篇《五分钱的浪漫》:我想把这篇文章中的文字当成一种特殊的硬币,撒进原本就具有浪漫天性的文字中。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