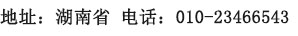于右任與後碑學時代的碑帖熔冶
文/王曉光
于右任的碑體行楷書
碑學後期書家中,行書卓然自立者,當數趙之謙、于右任等人。趙、於行楷的共同特點可概括為“以行寫碑”、“以帖入碑”,讓硬朗、鋒利、有時顯得板滯的魏碑體“流動”起來。于右任“以行寫碑”並留住北碑的雄健、奇險、樸茂感,是他的一大特色。
從用筆用鋒上看,于右任的碑體行楷主要是圓筆主導、時用側鋒。于氏早期魏楷追摹魏碑刀痕效果,像年代前期的《張清和墓誌銘》、《贈大將軍鄒君墓表》等,均方筆為主,鋒棱顯耀;伴隨著之後不久自家碑體行楷風格形成,他轉而越來越青睞圓潤樸厚的筆觸,而放棄了對碑楷刀鋒效果的追求,不論是草、行、楷書,均改以圓筆為主了。筆圓字方、魏碑體的構架、篆籀式或帖派的筆法,成為于右任行書的點畫特徵。其碑體行楷裏,用鋒是多變的,不止于中鋒,還常出以側鋒刷掃,以強化“書寫”意趣,這在其後期行書中運用得更多、更靈活,如《樹德立節聯》、《行修理得聯》等作。
從點畫細節看,于右任行楷書突出誇張一些筆劃以凸顯特色。于右任碑體行楷之所以個性鮮明,與書家個性化的細節表現有關。比如,依據北碑斜畫緊結的體勢,借取北碑代表性的特色筆劃(斜長撇、捺及折部、橫筆等),應用到自己的創作中。於書的主橫畫較長,且呈曲彎狀、向上拱起,一波數折;長撇、長捺基本來自魏體,撇一般長於捺,築成三角形字形;“口”類部首常封閉緊密且左高右低;“辶”部仍依北碑之形,厚重且收筆上挑……但這些借取絕非簡單挪用,而是以個性筆法寫出,它們在於右任書作中並不突兀、另類,而是與其他筆劃、與全局構思融為一體。
從結構上看,于右任行書頗具特色:奇崛而複歸平正,拙中有巧,活用魏碑體勢,自成風格。
從章法上看,于右任行楷書分兩種情況:楹聯和條幅。楹聯作品如前所述,講究字間的正、欹關係,並以長短、粗細筆劃來豐富點線變化,求得通篇獨特效果與氣息貫通。條幅、條屏、中堂、橫卷類作品(以多字數作品為主)中的正欹變化相對單一些,一般均做左向傾斜,以期全篇字勢上的統一感,其中的單字不似對聯那般講究完整與對稱感,而是失在局部、得在整體,追求的是章法上的和諧統一——這也是書法大家們在作品佈局上的共識;此外,條幅類作品常通過粗細筆、濃淡筆、行草體相間等手法尋求節奏變化、豐富視覺效果。
于右任的前、後期行楷亦有不同,前期魏碑風貌更濃厚,方直字勢顯著,後期魏碑味逐漸淡化,筆觸愈加圓厚,揮灑更自如隨意、自出機杼。從“碑”的角度看,于右任後期行楷書“碑骨帖魂”的特色愈加散發出來,此時的碑意不再是“形而下”的,而是化為一種“勢”或“意”存留於字中,給人以一種碑的感覺和氣象。于右任後期行楷類作品更多地運用了帖系筆法與書寫理念,北碑意味或存於部分細節中,比如主橫畫、“人、乂”結構、“勿、宀、冂、口、辶”等部首間;後期行楷書更多地強調了“書寫”意味,更突出了于右任式的“韻”,正像有研究者說的:“融篆、隸、草、楷筆法於一爐,以中鋒為主,參以折筆、斷筆、截筆、頓挫、波磔之法,縱橫揮灑無不自如,其運筆淺入平出,不拘藏頭護尾等傳統理法,放得開,收得住,真可謂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用筆雄強大氣,自然真率。”[3]草書亦自然帶入此時期的行書中,行、草完美融合,如《杜詩三川不可到橫披》、《杜詩豪俊初未遇四條屏》、《陸遊醉中懷眉山舊遊四條屏》等,間草間行,字字不連卻氣勢貫通,縱橫馳騁,氣勢壯闊。
于右任草書
于右任草書點畫用筆以厚潤渾樸的圓筆為主,這是他自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書寫風格大體確立後持之以恆的用筆法,草、行、楷皆然,草書尤為突出。不像行書中有時輔以側鋒,于右任草書專注于中鋒,時常給人以篆籀般的厚重感。於氏草書線條或可上溯至唐懷素(—)“鐵線草”,但於氏線條較有粗細、直曲等細部變化,而非一味地筆鋒單面平鋪,也非粗細一律的單調線條,於書尋求那種無意於顯鋒露芒下的中鋒筆觸多變性。一般來說,晉唐草書名家中,單字不連屬的範例是王羲之、孫過庭,連綿草的典型是王獻之、張旭、懷素,不論是字間少鉤連的小草,還是筆意綿延的大草、一筆書,行筆中的點線多變性總是書家們的追求。于右任草書執著於字字不連的小草類型,那麼每個字就作為整體中的單元或細節被重點刻畫,然而單字的完美、到位並非高超藝術家的追求,于右任草書單字雖不乏點畫細節多變,但它們顯然更傾向於服務作品整體,即便單字、細節有所“缺憾”,卻成就了整體和章法上的要求,這也是于右任草書從細節到整體章法完美動人的重要原因。
在結構方面,于右任草書營造一種簡疏、空靈之美,形散神聚,簡淨而奇險,進而形成兼具“豪氣、清氣、逸氣、稚氣”(鐘明善語)之獨特書風。于右任草書單字結構疏空、簡約主要來自以下手法:其一,字內點畫間並不講究緊密銜接,而是常常分離,字的中宮一般較空疏;左右結構的字,左右兩部分留有一定空間;上下結構的字也常這樣處理;這與其碑體行楷書的結構正好相反;然則單字筆劃並不向外拓張,而是普遍有向字內部回收、扣抱之意,如是形成字內部空疏、字外部縮緊內收的情態,故而整個字仍屬內擫型。其二,簡化字結構,以盡可能簡省的點畫構成草字,字的筆劃結構能簡就簡、能省就省,力避字內結構繁瑣、筆劃糾纏。這種做法與年代漢字拼音化、簡化運動,特別與于右任年代標準草書運動,關於草書符號化、簡化、準確、美觀等的提倡都不無關係。于右任簡約式草書中淨化的點線更純粹、更明,更有益於形式感的創造,這與王蘧常結體簡約的章草追求頗相似,而與清初傅山、王鐸等的繁複化的行草書正相反。
于右任在草書創作中曾提出“四忌”:忌交、忌觸、忌眼多、忌平行。其中,“交、觸、眼多”說的是一種情況,即指點畫過分密、繁,結構上過多縈繞、過於複雜。字內點線交錯、觸連、碰撞,若曲弧筆過多,則易形成大量的“圈眼”,這都是結字、筆劃太過繁瑣或連筆、引帶筆過多造成的,這種寫法是于右任反對的,與他的簡約明瞭、白多黑少、極少牽絲引帶的草書結字法相悖。
清末民初碑帖融合風尚
清前期的訪碑、學碑、寫碑行為引發尚碑運動及碑學興起,清乾、嘉時期碑學走向興盛。就碑學審美情趣及理論導向的變異而言,清中葉以來出現了兩種變化:一方面轉向對“古質”、“沉厚”、“金石味”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是尋求碑與帖在創作上鉤連、融合。阮元、包世臣、劉熙載、康有為等理論家對碑學實踐做了理論上的宣導和總結。
阮元雖強調“古”,其南北兩派論並非一味偏執、保守、厚古薄今,而是持二元並存、包容兼顧的態度。他說:“是故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16]他較早持廣泛取法、碑帖相容、借古開新的態度。包世臣《藝舟雙楫》“在揚碑的同時,並未否定以行草書為主的帖學,而是在強調辨別真偽的基礎上,熔冶碑帖。”[17]劉熙載《書概》進一步強調對歷史書法遺存的包容性,貫串碑學與帖學既對立又應該相互交融的思想,他說:“南書溫雅,北書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諷詠,北如斛律金之《敕勒歌》。然此只可擬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眾才者,風氣固不足以限之。”[18]康有為在自己的論著及書法思想中既有對北碑的激賞,又反復強調“變”與標新,“變者,天也”,他用自己的創作闡釋“變”的含義以及碑、帖糅融的價值。可見,清中葉以下碑學理論脈絡中,一直存在著碑與帖熔冶的呼聲,這聲音越來越響,甚至演成晚清書壇主要審美與創作思潮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碑帖交融成為碑學書法創作的新熱點和新趨向。
從趙之謙到于右任、王蘧常等,後碑學時代的碑、帖熔冶型創作或可做以下歸納:
從用筆風格及點畫效果方面看,大體可分為兩種風格:以趙之謙為代表的精緻表現型,以沈曾植、于右任為代表的粗放渾樸型。碑派書法總起來說是崇尚雄放、粗樸型筆觸的,趙之謙的以行寫碑重回帖學講求精緻筆法的道路上,這是一種矯正;于右任也有類似的追求,即在寫出大氣磅礴、筆墨淋漓點線同時並未放棄豐富細節的表現和對用筆的關注,傳統的筆法上的意義仍作用在於氏書作上,比如其碑體行書中側鋒效果,比如其草書裏多變的線質等等,這實質上屬於碑、帖兩派技術的折衷性處理。
從碑或帖因素的技術攝取角度看,我們寧願將趙之謙和于右任歸為一類,在著意表現碑的體架、帖的筆法方面均勻用力,他們的創作(主要是行楷書)其實均勻照顧到碑、帖兩方面技術,讓這兩種因素在書法裏均有呈現,像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硬指標”,當然這並非生吞式的“消化不良”,而屬於一路藝術創作類型,用“碑骨帖魂”概括兩人風格非常貼切;而沈曾植汲取傳統的“雜”與“廣”成就其全新的個性面貌,漢隸簡帛、北碑、米芾、張瑞圖等在其章草中已被熔化得不見形跡了;其他書家,康有為將魏碑體化作一種氣勢追求,王蘧常主要把篆籀漢隸氣息融於自己的點線中……
碑學興起後書法史出現了雙峰對峙局面,碑學的進一步發展使碑與帖從對立到糅融成為必然,從趙之謙等晚清書家的熔冶碑帖開始,到于右任等為代表的個性創作,幾代人的探索留下了多種多樣的碑、帖融合的實踐成果,其中,“新”與“理”乃是這些探索的靈魂,“新”即是創新,“理”即是合于書法創作、創新之道理,是合于書史發展之規律。于右任等人的作品,不僅在碑學風格史、碑帖交融風格史上寫下亮麗篇章,也給當代書法創作很多啟示……
(本文刊于《中华书道》年秋季号,此处为节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