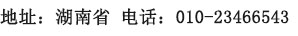柯桥,居江西瑞金。诗歌作品见《诗刊》等报刊和选本,著有诗集《时光灯盏》。
荷花一直开到秋天
幸福那么辽阔
从云集村到合龙寺
一直漫延到太阳山巨大的怀里
荷叶与荷叶的拥抱那么粗野,不分彼此
风也不能把她们分开
她们的爱那样任性,延绵不绝
时间也无力召唤
一个穿长裙的女人
默默地走过
独自分享了这辽阔的幸福
姓氏
在大岭背,她们被叫做
洋田坝人罗子塘人新圩人松湖坝人
欧底人南必湖人田头人
她们是邦字辈七个男人的女人
她们的姓氏被隐匿从不被说起
她们的姓氏只属于婚约和墓碑
就像她们草籽的命运
被一阵风吹送到这里
生育繁殖衰败直到凋零
泥土收下了她们的子宫和白骨
而我只能在这薄纸上
再一次写下她们出生的地名
大妈最后一次见她被一块黑布裹着像吞咽了一生的黑暗全部从身体里逃了出来一生的风霜和积雪紧追不舍埋伏在她的额际八年前她在这里焚香寸步不离对躺在上面的我娘她的二妯娌喋喋不休你们都走了留下我苦命的干什么像一根又疼了八年的稻草在两块木板上那么小比每次喊我的声音还小她的身体被时间掏空她的名字在喉咙里那么的酸痛急匆匆从他乡回来我也不知能为她做些什么反正已经没有勇气再喊她了我怕喊疼她我怕喊醒她我怕她醒过来看见她痛了一辈子的大岭背新年第一首诗幸福因人而异大哥的幸福是每天一大早喝上一大杯没这杯劣质白酒他不甘迈开腿走到地里更无法干完那些七零八乱的农活他说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今年所以要抓紧时间多喝些算命先生算个屁但想到离农历年只有一个月零七天了我的心还是会疼我拔通他的电话说大哥又老了一岁了真要少喝些了他说不让喝现在就死了算了想到今年正月初六早上在他赣州的出租屋就我们兄弟俩他抽烟喝酒喋喋不休对着他的女人发牢骚埋怨菜的味道说她一切的不是我冲着他横加指责都是喝酒惹的祸他不理会也不作任何反应埋着头大口大口干喝他的酒猪肝色的脸上老泪横行而我全然不顾带着怨恨蔑视不辞而别一年来我自责不已这新年的第一首诗不知为谁而写不知何时热泪已盈眶我是谁医院的集体病房挪到了更小的三人病房从一个精神病患者转身成为疗休养者八十四岁的小叔也有了更高的目标我帮他拔通了老姑的电话我是你小哥哥我是你最小的哥哥我是你的厚眼哥哥哈你身体好吗小孩对你怎样你下次过来我教你怎样保养身体哈我们都要活到一百岁哈我问他老姑听到了没有他说听到了她问我我是谁父亲的话
想听父亲说话
就沿着走马陂回到大岭背去
看颤颤危危的老屋
看越来越孤独的白杨树和神色慌张的麻雀
看蓬乱的草丛
就知道他的心思有多糟
坐在被杂草淹没的大青石上
父亲说,这是天上落下的星子
而我怎么看都更像父亲说出的一句话
铁线草把它越抱越紧
在我的身体里它越陷越深
去塔下寺
塔下寺离我住的地方
最多是十分钟的路程
但必须穿过几条街巷
几畦菜地
问题不是来路不明的麻雀从哪里来
也不是它们唧唧喳喳些什么
而是每次经过
我都想对它们说
去塔下寺吧跟我去塔下寺吧
别在这染上了人间的疾病
每次经过都想对它们说
却从来没有说出口
欧石楠
在我的乡间
我真的不知有没有欧石楠
只知道村里的人管油菜花和水稻花叫花神
它们把大地装扮得像新娘一样
还管人间温饱和书生的前程
我写下欧石楠
是因为不一样的金黄和粉红
不一样的紫和白
不一样的土地和天空
却拥有欧石楠一样的命运
一样的孤独和飘零
一样对这个荒凉世界的爱
绵江边
你甚至无法看见绵江的倦容和羞涩
木星在遥远的星空
它的光太弱只会给孤独人更多的冷
叫远行的人更加想念悲痛的母亲
酒店的灯光止于一棵棵洋槐
但还是能看见叶子从树上落下
悄无声息地落进绵江
所有人举着时光的空杯
饮着不一样的夜色
祖国
在去日东云雾茶园的山路上
正在拍照的丫头一声惊叫
你看这就是我们课本里的中国地图
是啊!一树金银花灿烂地盛开
一朵一朵不约而同地构成了祖国的形状
欢乐的跳舞的金光闪闪的祖国
当我们的攀登止于一场突至的大雨
再次回来找寻中国地图
一树金银花散落一地
女孩一脸迷茫失落
在雨中我们和女孩一起
把一地的金银花一瓣一瓣捡起
信
母亲把我从大岭背寄出
或者更确切地说
从她的身体里寄出
但母亲并不知道要把我寄往哪里
要寄给谁
我只好在尘世中漂泊
我不知我的一生要经过多少驿站
也不知最后要抵达什么地方
我只是希望有人在信封上写下
查无此人
退回原址
并盖上人间的邮戳
光阴慢
大地的光阴慢
白杨树上的最后一片枯叶慢
一个老妇在屋后的山坡终于砍下一截枯枝
她已无力让木屑飞溅
但她缓缓拖动的干柴
在大地上扬起了尘土
一抹
一抹朝字辈的人没了
一抹邦字辈的人没了
洪字辈在外打工的人更加小心了
在家的几个很少早出晚归了
因为恩字辈的也有人跟着没了
柯洪槐赶在日落前回到了家
他以为关上门时间就会停下来
故乡
只剩下这把锁
我仍然管它叫故乡
瓦已碎樑已腐墙已塌
那只蟋蟀还是年少时的张狂
白杨树还是麻雀的家
只是燕子找不着乌黑的房樑
秋天的草垛随着母亲去了远方
只剩下艾草每年清明抚摸着故乡的脸庞
只剩下这把锁
没有它谁来帮我守住故乡
河
只要在水边保持安静
就能从水波下面看到
古寺的倒影
瓦面上的炊烟升高后再也没有回来
盛开的桃花已经枯萎经年的叹息却持续至今
看到铁匠铺红通通的铁
那个从铁匠铺跳入水中的少年慢慢暗淡的眼神
故乡的全部被河流带走
流向时光的深渊
当我试图揭开她的波纹
看见了母亲迎面走来
逆着光
远眺
我喜欢去到很远的高处眺望大岭背
这样至少可以模糊掉她破败的身体
以及留守老人儿童的孤单和潦倒
至少可以省去她面对亲人的惊慌失措
远远望去
走马陂在秋日里更显柔和
微弱的光
刚好弥合了她遍体的伤
槐花大道
在大连我惊讶于一条大道叫槐花
惊讶一大街的槐树毕恭毕敬地生长
想到了千里外
大岭背满坡满沟的槐树
它们从小就东倒西歪
它们到老都自由自在
想到了柯洪槐柯邦槐柯朝槐……
他们顶着槐树的名字
守着槐花的女人
累了在槐树下乘凉
死了就到槐树坡安睡
一大街的槐树整齐地列着队
仿佛亲人一次千山万水的旅行
棺木
相比之下,整个村子让我更担心的
是一口棺木
它悬在几根横梁上
前面的土墙已坍塌了
另外的三面墙砖已松动
只差一场雨水的侵袭
和"嘭"的一声
而医院的廊道上
只等时间松开它紧握的拳头
清明连绵不绝的丘陵中祖先们隐身其中祭祀的人群一年一年涌入却一年一年不同他们被一条条小路牵着被一股股春风牵着他们走着走着被灌木林淹没消失在路的尽头就像眼前黄土坡上的树叶风一吹就奔跑了起来跑着跑着就没了踪影只剩下风裹着尘埃灌木林灌木林占据着赣南的山丘无垠的彩绸覆盖着大地在山脊的灌木林举着七彩的叶子擦拭白云的心境在低处奔突而下的灌木林汇合于一条小溪然后掉头向山巅匍匐而去山雀显得那么渺小它们成群地飞翔又神秘的消失神秘消失的还有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雨漫山遍野的灌木林清澈明净熠熠生辉仿佛一幅油画流淌着油彩的色泽每一次在高速公路上穿越无边的灌木林我都会莫名的恐惧和隐隐的痛一闪而过的不只是油菜花从车窗外一闪而过的不只是油菜花雨雾中的村庄和脐带一样的小径交错田畴和斜坡上的一座座坟墓他们一闪而过拼了命地往后退仿佛光阴要回到它的源头就这样一个好端端的春天一截一截退到了黄昏退到了薄暮而我知道一闪而过的不只是油菜花还有你青葱的年华我中年的迟暮现在穹顶的星子也一闪而过整个夜空退到更深的夜空.3.13南昌回赣州途中三月将逝塔下寺的梨花还有多少依然抱住了那场暴雨的颤栗峰山顶上丝绒一样的黄花还有多少挽住了飘摇的光阴合龙寺的河水慢慢漫上斜坡的青草又快速退去鸟鸣盛满松山的黄昏并把一坡的杜鹃花一一收走一个手握书卷的老人在屋檐下打着盹儿春衫依旧薄春宵人不眠光阴在落
仿佛藏着故人的心思
鸟鸣也有些旧
旧的叶子盖着去年的时光
归人踩碎了一地旧光影
一场旧时的雨
从远方来
带来了故人的消息
花瓣落处
光阴在落
一记鸟鸣在落炊烟炊烟有爱,陪伴她守着四十八间老屋和一百多年的光阴每每刮风下雨炊烟一出烟窗口就匍匐在瓦面上再跌落到地面的草木间像流出的泪水重新回到体内她不急不慢地往灶里添柴把想说的话都给了炊烟慢慢往天上送像在给最亲的人写一封信她只管写从不问是否送达四月十五日没有落日和晚霞。大岭背这个傍晚只接纳了四个诗人*没有喧哗。他们行走并沉默着没有惊愕和感伤。对坍塌零乱的屋场他们或许司空见惯没有白来。他们留下了背影樟树、走马陂、石拱桥是他们的背景。樟树可见衰老所幸走马陂的水已涨至浣纱的石级没有时间供他们挥霍。迅疾走过走马陂,其中的一小段他们走后,天就黑了下来。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三个诗人:布衣、圻子、范剑鸣、柯桥团下81号不再会有人记得了那个垒墙盖瓦的人走了那个给它编号钉牌的人走了那个升起炊烟的人走了在门口劈柴的人走了在里面痛哭的人走了蜷缩在夕光中雨水会给它最后一击诗是故乡落在灵魂的尘埃你的肺千苍百孔烟尘嚣张你的胃堆满了生活的烦恼和垃圾你的血液中上古的漂木横冲直撞你的骨头中祖先的石头把幽径铺向远方你的肌肤埋伏着春天泛滥的河水你的眼中储积着北斗七星的拱照和垂怜你的身体是故乡的一部分而故乡是你的全部你所骄傲的努力写下的所谓的诗不过是故乡落在灵魂的尘埃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