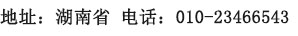菜园小记
——种菜,一种确定的获得感
平生喜爱种菜,亲手劳作,来自土地的收成,诠释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素道理。
人生别处不得,菜园里的劳动却必有所得,让我来道破所有回归田园人的心意吧!
(一)
陶渊明,种的是菊花,他那块地,换在我手里,大致我是不会种菊花的,一定要捣腾得菜蔬盎然、果木葱茏。他玩的是心情,浇灌和采集的是意境。
板桥这人实在,种竹子。他爱画竹,图的是实践脚踏实地的创作。“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他还搞了立体种植,属于文人做农民的高段位。
当然,陶渊明也不是五谷不分,他也种菜了的,只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地里有点荒芜。你看他给自己起的雅号:五柳先生、昌黎先生,这些都还接地气,突然又来个羲皇上人,突然又拔高了。他这人,整个就是玩的心态。
不过,他讲出了一个菜园子规则:田间管理,胜过千言万语。在菜蔬和庄稼没有长到蓬勃葱郁之前,除草是个永无休止的活路。生长季节,草总在和禾苗的生长竞速中拔得头筹。
坚持种菜好几年了。有一年偷懒,地荒芜了,当年草籽落地,给今年的栽种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铁线草、马草、狗尾巴草一茬茬长,每次到地边,第一要务是拔草。一分地而已,和老婆两个人要忙活一个小半天。除草劳动可以换来周末一次高强度的体力付出。
对草和豆苗此消彼长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这个角度来看,陶渊明却是我的远年知音。我们的懒散,都得到了土地适当的惩戒。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放任了草芥,就该品尝这一层烦恼。
(二)
种植稼穑,起意是为糊口,为延续人的肉身,让土地和粮食、蔬菜的合作,满足人们的口腹。
看过一个报道,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授拿不到薪酬,就在荒坡开地,解决口粮,这还不行,没有活钱,教授们纷纷养猪。大学后面的山坡,满山是菜蔬,教舍背后猪圈陈列,生活气息一时洋溢。
不要觉得有辱斯文,特殊年景下,比起饿死人的时节,这个又算得了什么呢?
据说清官海瑞就是一个养猪种菜的高手。那时一个县太爷的月薪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元,养儿伴老都不够,更不说送娃出去读书,或者要在城里按揭一套像样的房子了。总之很作难。他就种瓜种豆、养鸡养猪,据说他的那个县衙,其实在今天来看,就是一个田园中的办公场所,特色办公小镇,被绿阴、菜园和油菜花田包围起,受看得很!
因为他一分钱红包都不收,全靠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官当得清白,也成了操持农事的高手。
要在今天,他才是真正老百姓喜欢的网红。
庄稼和蔬菜从糊口的基本功能站起身,沿着时光的青石板小路走过来,在不同人群的体验中,具有了不同的格调与风格,从广袤田野、现代化种植大棚、屋顶花园、阳台旮旯,都得到了合适的安顿。
对今天居住在城市水泥森林中,更多有种植冲动和农民情怀的人来说,腾挪一点空间,种点绿植菜蔬,是工作发条的一处停顿,生活里的一抹绿色。
(三)
那片菜园,在40多公里的郊外,一处房子的侧院。
最先做的却是开荒的活路。从开挖草坪、清除建渣,到后来的土壤改良、肥力储备,接近两年的调整,让那块贫瘠的土地,逐渐焕发出活力来。
第一年,在农贸市场采购了蔬菜种子,没有施任何肥料,圆白菜、上海青、玉米获得丰收。每次去,都能带回很多青菜,用焯后清炒的方式,带有一丝脆甜的口味。到糯玉米收获的那次,装满汽车后备箱,一路给亲戚派送。
劳动不必分享,成果好像却有分享的意义。
第一年草没有困扰到我们,随后种南瓜,蔓秧像淘气孩子四处爬走,地里已经容不下其他作物。疏于清除杂草,它们获得了极大的空间。这一年,南瓜丰收了,记得收获了15个左右金黄胖硕的海南大南瓜!
有些杂芜的事物,你不能给它肆意滋长的机会。野草就是。第二年失去田间管理的地里,留下了生命力顽强的草籽。后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
菜园需要精心的护理,更重要的是精心的种植设计。根据地力或者阳光照射,来布局不同的品种。是撒播种子,还是用菜秧?都会有不一样的收成。我用当年收下的玉米做种子,第三年玉米苗长得高高矮矮,像一群先天不足的孩子。落在地里的白菜、上海青种子,复发后一律营养不良,长不出肥硕青葱的样子来。
尽管,这一年,我们用上了油楛、酵素,没有预期的收成。
伺弄菜园,即是打开一种心境。那个叫老树的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用文人画来这样喟叹城乡之间的陌路:“少年住在山里,抹黑都知归路。如今混迹城中,身心没个去处。”
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乡土文明浸淫的社会,现代人对生活的理想主义,会像蜻蜓一样,轻盈停留在水波潋滟的田园生活上。
我们都会相信那里才有我们内心的声音,那里才是心灵最后的归处。
小刺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