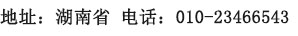1
记得那是年的一天,棣花巩家湾我老表巩述理过一岁生日。母亲领着我们去祝福。因为丹江河水上涨,河面宽阔,没有桥,只能坐船过去。我还在母亲怀里吃奶。撑船的是我们自家人,我的伯父顺佰。我对他的高个子、大鼻子印象深刻。后来听母亲说,我们是从商镇堡子村逆行到巩家湾的。顺佰家住在我家的后门,也就是当中院。他为人憨厚老实,也会多种手艺。比如:打铁、做牛皮绳、还会熬胶。那时候,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儿经常在他家看他打铁。我家后门口,有一条多米长的一条小巷子。夏日里,既通风又凉快。每到饭点儿,左邻右舍的村民都端着碗筷来这里乘凉,谝闲传。南边儿房檐下有一排摞放整齐的石头。人坐上去,又稳实,又凉快。乡亲们在这个聚会乘凉的地方,说家长里短,谝大事小情,非常热闹。我们这些小屁孩儿也就经常在这里玩。比如:我们玩泥巴,用泥来摔泥瓮、捏小汽车等。
每到夏天,天气炎热,吃过午饭,我们十几个小伙伴儿光着屁股,一丝不挂就跑到丹江河里游泳去了。记得有一年,还是槐花盛开的季节,天还有点儿冷,我们几个玩伴总在午饭后,老远就互相心照不宣,做个游泳的姿势,便偷偷地跑到丹江河去玩儿水,也叫打江水。河堤全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大约有一丈多高。有胆大的就不加思索地跳了下去,胆小的才慢慢儿下水试探。夏季,几乎天天如此。有时候,一天要去河里好几次呢。我们还拿着自制的铁条儿满河里打鱼,在石缝里摸鱼,尽情地玩着水,玩累了就上岸。大家都光着身子,上树摘着吃槐花,也不嫌刺儿,也不嫌脏,摘下来就吃。
那时候,村子里丹江岸边有四个石鳖,大家约定俗成,一号石鳖是女生玩儿的,二三四号石鳖是男生玩儿的,打江水、洗澡的地方。水是很清的,满河里都是人,妇女们都是晚上去洗,月光洒在水面,波光粼粼,夜晚的月色令人沉醉呀。一号石鳖,那里有一棵大柳树,有一个大水塘,那时候,家里都没有洗澡的地方,没有那个条件,全村人都在这里洗。那时也没有空调,人们可以在水中乘凉。河水中间,有一片河滩,那个河滩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人们大小便的地方了。记得满河滩上都是粪便。人们走在上面,都小心翼翼,生怕踩到脚上。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村里刘塬上的刘军福和周塬上的周金山在河滩上打起架来了。他们互不相让,在河滩上翻来覆去,两个人硬是把地上的屎,你给我用手往头上扣,我给你往头上扣,一片沙滩上几十堆屎,不大功夫,让他俩给扣完了。没有人上去劝架,一来嫌太恶心了,二来也是害怕把屎不小心扣到自己身上,只能远远地站着观望。当然,也有劝架的,可是他们俩哪能听得进去呀。
还有一次,发生在我身上的小事,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感到很窘迫呢。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正是收麦子的季节,我哥周中礼收麦子回来后,一个人在河里洗澡降温。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儿光着身子也去打江水。我却并没有注意哥在河里洗澡。我第一个冲在前面儿,嘴里大喊到:“河里有一只大乌龟。”然后,就不加思索地跳进河里去了。只见打得水花四溅,我吓了一跳,心想:哎呀,真是个二杆子,肚子都碰得有点儿疼了。逗得大家哄然大笑,而我看到哥的一瞬间,尴尬极了,我只有低头不语,因为我无意间竟然骂了哥呢,还好哥大度,很关心地问我:伤着了没有啊?
2
年,正是吃食堂的时候。在我家前面儿有一个大院子,里面住着五六户人家,就在那个院子里建起了高烟囱大锅台。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去打饭。做饭的厨师有李如林、刘玉江、刘新发等。我父亲周定民,当时是保管。因为他比较有文化,以前在洛南县政府统计科工作。只因为有一次,下乡回来汇报时如实汇报,比如:农村人生活苦焦、日子过得把作,等等。领导说,我父亲是右派言论,要隔离审查。我父亲一气之下便自动离职,回家务农了。后来,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我父亲,记得他每个月都能领取生活补助金呢!我父亲是一个爱学习,爱听广播,也爱看报纸的人。大队小队丈量土地都离不开他。他还打得一手好算盘,用手绘出了全大队的土地图呢。
当时,吃食堂是把每家的粮食收起来交到集体,比如:红薯片子等。家家砸锅,家里只要是铁的东西都要交给集体大炼钢铁,大队院子里盘着高大的泥炉子。那时人民生活非常的艰苦,用麦秆打成粉也能充饥。我才不到四岁,经常去食堂那里玩,几个做饭的厨师常逗我耍,偶尔也会给我吃些东西。大跃进时期,母亲也是天天上工。母亲名叫巩水芹,两岭村河对面巩家湾人,跟了父亲以后,生育了我们弟兄姊妹五个,她一辈子善良、勤劳、从不见发过脾气呢。她劳动的时候,要把我带上,很是辛苦。生产队要盖厂房,母亲担着笼担,去刘源上老四队的庙嘴子窑上,把瓦和男劳力一样,一担一担地担着出力流汗。我手插在连带裤子的胸前,跟着跑来跑去。记忆中,母亲还很年轻,头上扎着长长的两个辫子,高高的个子,只见她担着两笼子瓦,一次又一次地跑个不停呢。母亲也很疼爱我。记得我当时戴一顶红灯芯绒帽子,上面有一圈儿银碗碗儿,中间有个银老汉人儿。脖子上戴着一个银项圈,上面带着一个大银锁,还有很多小铃铃呢。我很淘气,也很幸福。母亲每次上商镇集回来都要给我们买好吃的,不是沙果就是梅子、桃子、杏子、白兔娃瓜等时令水果。所以,我每次都要在上场里等母亲,那里有一棵大四方柿子树,我就坐在树下等母亲回来。每次母亲回来都要从井里打一桶新水,把甜瓜放在桶里冰一个小时后取出来,用刀切成小牙牙,吃起来又凉又甜又爽口。
那时候,平常人们都穿自己家做的粗布衣服。冬天,我们只穿一件棉袄和棉裤。也没有衬衫和线衣,一冬下来,棉衣棉裤到处都是黑明垢伽,又破又烂。袄袖子上黑脏黑脏的,身上的虱子有时都能摸捉出来。大家都一样,谁不笑话谁。
记忆中,母亲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中年妇女,在家里可以说,是一个贤妻良母,当时母亲在生产队上夜以继日地劳动,爱加班儿干活儿,思想上也努力寻求进步,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家里,还要做很多家务活,一日三餐、洗锅抹碗、织布纺线、洗衣服等。我还很小,只能给帮个忙,锅下搭个火。做简单的饭,有时帮忙洗锅。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吃少,少吃。我们也算是一大家子人呢。每次,母亲烙一个白膜,一个黑馍,母亲给父亲和大哥分多一点儿,因为他们在劳动,太辛苦,剩下的给我们分少点儿,给她留得更少一点点儿,并且是黑馍呢。
3
那时,我们也在托儿所上学,也叫幼儿园,幼儿园设立在十字路的北院,那时很幼稚,做各种游戏,唱各种歌曲。玩具很简单,有哨子、响棒槌、小鼓、小皮球等。游戏有传皮球、丢手绢儿、捉鸡娃,还有荡秋千、压油油、翻杠架、骑马马等。我们当时吃饭只有稀饭、馒头。唱的歌曲有,樱桃好吃树难栽、雄赳赳气昂昂、拔萝卜等。后来,等我到了七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学了。一二年级是在戏楼和李家祠堂度过的。在一二年级时候,我总是爱打爱闹,不用心听讲。彭芝逢是我们的班主任。放学后,回家还要帮大人干点儿家务活,给猪掐草、洗锅、扫地等。冬天上学,每人提一个小火炉,早上起来,都要偷偷地把柜子慢慢掀开,生怕响动,不能让大人听见,装上两兜兜玉米,有时候,偷些红薯片子。放学后,同学们聚在一起,然后把玉米埋在热灰里,熟了以后用小木棍棍儿搅一搅,你争我抢,品尝着自己做出来的美味。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没有电器,大人把好吃的馍馍等熟的食品,挂在空中的笼子里,每次偷得取过后,把挂在空中的篓子再用手慢慢儿地稳住,不让它再动,害怕大人看见了骂我们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想吃啥都有啥,还害怕孩子不吃饭儿。那个年代,黑馍馍、白馍馍、做过豆腐的豆渣馍都偷得吃。红薯片相当于现在的饼干一样的东西。红薯、白萝卜相当于现在的苹果。糖精水相当于现在的饮料。稀饭上面的油油相当于现在的奶粉呢。家家户户不过年都吃的是黑面,早饭是蒸红薯,再坐一盆酸菜。条件好的,烧一点儿白菜玉米面汤,中午就是黑面、玉米面,红薯藤蔓稻皮子糠推成面,用柿子一拌再推成面就能吃。有的还吃树皮,上山摘冬青叶子、石兰子等吃。村子里有一个叫山正的人,爱说顺口溜,结果被批斗了好多次。他说:“哒哒滴,滴滴哒,社会主义好咋啦,稻皮子红薯蔓,把人吃得拉血串。”还有人说:“毛主席万岁!灌油先让我站队。”那时候,灌油买洋火都要站队,一次只给供应一斤半斤。记得,还有一位老年人说:“给他三个白馍,蘸着尿水他都能吃下去。”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米饭,平常吃米饭是用酸菜炒,只放一点米,主要吃酸菜。下雨天没雨鞋穿,都是光脚丫子,平时大多数,都穿得是草鞋。在学校里,本子翻过来写,翻过去写,为了省点买本子钱,老师带我们到操场用粉笔坐在操场上写。当时,学校还养了好多的羊、兔子,课余时间我们轮换着放羊,把羊赶到河堤上一边儿放羊,一边儿割草。回来时,背上一捆草到学校。那时候,一学期费用大概就是几元钱,剩下的是学校和国家来解决。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多,比如说,五一节、五四节、六一儿童节、元旦都要升国旗。搞活动时各种彩旗都有。文艺演出时锣鼓喧天,演出好多小节目。例如:王二小、张高天、刘文学等。也有跳高、跳远、篮球、乒乓球、跳绳、拔河等文体活动。还有帮红军烈属拾柴,帮忙干其他活儿等。放假了,星期天要帮家里干活儿,那个年代不管大人和我们大一点儿的孩子没事儿都要拾粪。大人担笼担,上集一样,拿着小铲子,提着粪笼,拿着小铲子或者小锄子到处拾粪。转街道串巷子,下河里上沟里,走到那里拾到那里。拾了粪,生产队还给过称记工分儿。特别是冬季稻田里锄麦苗子,男女老少几百人,没有厕所,人们就到河堤背后去解决大小便的问题。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儿躲在河堤背后。等到他们解决好了,我们就争着去拾粪,争先恐后呢。现在,时代变了,人见了粪便,老远就避开了,唯恐躲之不及啊。我们一伙儿,当时提着满满一笼子粪,心里很高兴,边玩边拾,有说有笑的。记得有小先、我、叔平、帮娃、述鹏、述侃等。我们还做过一些出格的事呢。比如,我把雷子炮绑个结儿,摔到粪里,让叔平和小先去点,一点就爆炸。可想而知,两个人满身满脸都是粪便,逗得大家又哭又笑。还有一次,我亲眼看见,水沟河村的一位大爷,上商镇集回来,用一页瓦片端了好大一堆屎。他的一只手还拿着二尺长得铜烟袋,边走边抽烟,逗得过路的人又想躲避,又想看,又感觉真好笑呀。
4
随着我年龄慢慢的长大,五六岁的时候,县上有社火表演。我一个人就偷偷地跑去看热闹,也没吃饭,也没装钱,那时家里也没有钱。两岭村到县城,来回要40多里路程要走。走到县城,也遇到了一些奇怪的事呢。西河的街道上,有几个人拿着小铁锨,还有尿勺,跟在大猪的后面儿,一直跟着猪走。我便感到很是诧异。后来看见猪拉尿拉屎。才突然明白,他们是在接猪尿猪粪。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太胆大了,现在五六岁的娃上学都要人接送呢。当时,回来的路上,我又饥又饿,眼前发黑。到商镇老君殿,跑到路边儿一户人家里,大娘给我喝了一大勺冷水,然后才又继续往回走,到家后实在没力气了,母亲气得又打又骂。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糊涂面,撑得我肚子疼。那是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
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后来,我经常去县里玩。有一次,听说县里要枪毙犯人周树友。还是我一个人跑去看了,当时我跑到车跟前,看见他是个光头,仰着头,瞪着大眼,被人按在车栏杆上,跟着卡车,跑到丹凤县城花庙背后,那里人山人海。他被枪毙以后,人们疯狂地跑去看热闹,真是太危险了。有几次,我险些被人流拥倒,害怕极啦,一旦倒下被踩踏,那就有生命危险。
我六岁那年,不幸得了一种奇怪的病。那天下午队上放工回来吃完下午饭,晚上加班儿推磨子,那个年代都是用石磨子推粮食,用石碾子推稻子。那晚上,我们一家人都在推,时间长了,大人送我回家睡觉,后半夜我突然觉得有两个人压在我身上,惊醒后发现两个人骑在身上,瞪着眼,当时我喊:鬼来啦,鬼来啦!两个人影马上跑到窗前,还一直在晃动。
父亲母亲被惊醒后,问我:咋啦?我说,窗门前有两个鬼,但她们是看不到的。我去尿桶小便后,刚要上床,那两个人影跑到床边,啊的一声,吓得我又喊又叫。从那以后,每天晚上睡觉都是如此。从此,我就在这恐惧中生活了两年之久。白天觉得满身被人抓,两位大人也很着急,抱着我四处求医问药,让好多医生给我看病。父亲是不信鬼神的,也没办法。母亲给我枕头下放桃木棍子,说是辟邪呢。可是一到晚上,天一黑,我就不敢出门了。父亲领着我,医院治疗,医院,我能记得医生给我做了粪便等化验。医生说,是身体虚弱,也是一种幻觉。大了以后就好啦,开了一些药。但是,还是没效果。后来,想明白了,才知道,原因可能是,之前队上死了两个妇女。我也去看了。年长的人说,是我看了死人,被鬼缠身了。那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后来也看了好多医生,也没有效果。渐渐地我长大了以后,就自己恢复正常了。
5
等到我七八岁时,我们一伙儿,经常去县城蔬菜门市部买笋瓜,二分钱1斤,一个大的就20斤左右,每次去都买一个大的,扛着回来。现在八岁的孩子还让大人接送上学,可那个时候,父亲让我和他步行去80多里远的铁峪铺二伯父家所在村子里去换粮食。父亲给我在背上绑了30斤重一袋米就出发了。下午,到了铁峪铺以后,走得我脚疼手疼,浑身都疼,第三天又背着30斤的黄豆返回。回来以后,我差点儿哭了,脚上打了好几个泡,浑身到处都疼。在那个年代,大人天天上工,基本上都把娃锁在家,人就上工干活儿去了。放工回来以后,有的孩子都从床上掉地下了,有的哭了睡,睡醒了哭,眼睛的眼屎多,鼻涕流得满脸都是,大人忙得也没有太多的时间管好孩子。我们大一点儿的娃们整天淘气侵人,不是打架就是害人。前村和后村的娃们分成两派打仗,用小石头、土蛋蛋、有的用弹弓、有的用玉米杆儿淘个洞洞把石子摔得很远。有几次,我的头上都被石子打得起了包。还有几次都被打烂流血了呢。白天,我们到四方岭上树吃蛋柿、摘核桃,或者就跑到堡子的桃园村偷摘人家的桃子和梅子。在当时,家里没有电视,没有电脑,人们没事儿都在外面游门子谝闲传。小孩子在外面儿打打闹闹,做游戏,玩捉鸡娃,做迷藏,有时拿农业社喊话的铁皮话筒搞宣传。也没有灯,点的是煤油灯,我们在学校宣传毛主席语录、元旦社论等。大家分工合作,报词的报词,拿灯的拿灯,喊话的喊话。结束后,又要拿上手电筒,满村跑得捉麻雀。家家户户都把红薯蔓子,挂在房檐下面墙上,冬天麻雀大多数都窝在里面取暖休息,用手电一照它们就一动不动了。一晚捉几十个,第二天把炮塞到麻雀的屁股眼儿里,点着,等他飞到高处就爆炸了。现在,想想我们玩得有点残忍呀。捉到老鼠也一样,塞一个雷子炮到老鼠屁股,老鼠跑着跑着就炸飞了。一天不是去河里拿铁条打鱼,就是河堤上捉毛老鼠,或者上树掏鸟窝,槐树有刺,很扎人,得爬上去把掏的蛋放在口里才能慢慢儿下来,有一次掏了两只小鸟,拿回家慢慢的养大玩。在村里还搭过人梯掏鸟呢。记得周叔平每次打到鱼就生吃。那时候,没事儿就到处浪荡,感觉很热闹,没有出外打工的人,人和人之间差别不大,感情深,人与人之间都是真情,你给我家干活,我帮你家干活。不论干啥,都是互相帮忙,互相帮助,从不说钱,谁说钱就和谁急眼呢。
6
村子里过年过节都要唱大戏。记得有一次,阴历六月二十九,村里过送夏节,来的所有领娃的客人,主人都要给娃烙互联馍(一种花馍),一烙就是十几个呢。队上杀猪卖肉,还有外村人来我村里卖各种菜,如:豆腐、茄子、西红柿、豆角等等。就和商镇集市上一样,热闹极了。中午和晚上,还唱大戏,记得那天中午唱的是秦腔《三世仇》,本来天很热,人们都穿个短裤,光着身子,我们小伙伴儿们也跑来跑去,打打闹闹。当时,有个叫西良的伙伴儿追着一个叫老五的伙伴玩耍,一下子没忍住,放了一个大响屁,裤子和腿上的稀屎流满了,逗得看戏的人乱笑,大家连看带笑,让他尴尬极啦。他又怪又羞,一下子钻进水渠,红着脸,洗起身上来。
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服,平时就穿草鞋和粗布衣服。拜年就用小圆笼,拿12个至20个馍不等,三捆挂面或者6捆挂面,条件好的就几块钱的酒、红砂糖、蛋糕等作为拜年礼物。压岁钱是一毛、两毛、五毛,最多的是一元。
一到腊月,大家就开始置办年货、砍柴、推米、磨面、换豆子、割肉。猪肉膘要越厚越好,最好是一手板那么厚,猪膘薄了没有人要。买回来炼猪油。那时候,生产队一年每个人才给分不到1斤油,炼的猪油将就着能吃一年。平常炒菜,没有菜油,剥几颗蓖麻籽,放锅里用铲子压碎,或者砸一个核桃,剥出核桃仁一压,就可以炒菜了。黑面馍馍、红薯面馍馍吃得多少人拉不下呢。腊月集上,母亲每集上都要背着大米去大峪沟散叉那儿,进行粮食交易,山里人没有米,坪里人没有黄豆,1斤大米换1.5斤黄豆,能换2斤包谷,1斤米换1.5斤红豆子,我也每次跟着母亲去玩儿。
腊月二十三左右,也就忙开了,要打扫厨房,房上房下齐齐打扫,去大峪沟的马拉沟半山腰挖白土,只有那里有,每年我们担着笼担,用小锄子一点点地挖。担回来以后,泡上水,搅一搅,就可以刷墙了,用长长的棍子绑个笤帚,由上面往下面刷。
腊月二十六左右,开始做豆腐,基本上大多数人,都要在队上饲养室里面儿养牛的地方做豆腐,因为那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铁锅,方便大家操作。每年冬里,家家户户也在这里窝酸菜,窝的是萝卜缨子、白菜叶子弄的酸菜,而且能吃上半年呢。做豆腐,一做就是半夜,等豆腐做成功了,我们也就开始吃锅底了,也叫豆腐网子。豆腐抬回家后,每年母亲就切一大块儿,用葱和醋一拌,一家人坐在一起,分享豆腐的美味。
接下来腊月二十七至二十八左右,开始蒸馍。一般一次要蒸几十斤面,一半白面一半玉米面混合在一起,有肉包子、有花卷儿、有糖包子、有鱼、有献祭馍等。从早晨起来,要蒸到中午,共计要吃一个正月呢。因为村里人说,正月不蒸馍。三十晚上更忙,炸油糕、炸豆腐、煮大肉、包饺子,忙完就快天亮了。我们小孩儿一夜不睡觉,等着啃吃骨头肉。偶尔大人也给一块儿瘦肉吃呢。也能吃些油糕、油炸豆腐。因为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吃上豆腐吃上肉。
每年过节,我都要去巩家湾接姑姑和外婆来。因为她们脚很小,三寸金莲脚,不方便行走,冬天他们爬着过桥,夏天我背他们过河,姑姑住几天就要回去。外婆一住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帮妈妈纺线织布,外婆那时已经70多岁了。
外婆每年9月20生日。有一年,外婆过生日,母亲花三元钱,给我买了一双雨鞋,结果一只在去外婆家过河时掉水里了,大家都跑上跑下找,第二天又找了一天,都没有找着。那时基本都是下雨天不穿鞋,一天一个工才分到一毛钱或几分钱,真是太可惜了。
当时,丹江河经常上下行船,一来就是几十艘,我们经常跑到河边儿,欣赏看热闹,车路上也时常从西安下来的马车,一来也是几十辆,有大骡子马,也去看看,看完了就提个笼子,拿个小铲铲,上四方岭给猪掐草。到地里后,有的就开始摔跤,有的就上树摘核桃吃,柿子成熟了就摘蛋柿吃。我们跑到惠家沟摘豌豆吃,又淘气又害人,一天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好是天真呀。
到了夏季,家家都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手里都是拿一把扇子。胳肘窝夹一个席片子,到大队大场里乘凉,有的娃们干脆睡在地上,睡一夜,有的在树上搭个凉架,人山人海。有唱歌的、有讲故事的、有说谜语的、有拉二胡的、有吹笛子的、有谝闲传的,好生热闹。下雨不上工时大人在家里面打草鞋,我们就给捶草、摘红薯叶、吃菜、拐线、学习。闲了,和伙伴儿们出去打牌、打纸包、丢窝等游戏。
到学校后,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也学打草鞋,造炸药,栽树种地。那时,大队也给学校分了几块儿地。编笼子、修梯田、挖地道,给红军烈属帮忙担水、抬水、扫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整天写大字报,批判走资派。邢俊明是校长,黑老大。记得,老师让榜娃和小先上去拉邢俊明的胳膊,邢俊明是大个子,身材很魁梧,他高喊道:“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我没有错!”手一举,一下子把他俩给举起来啦!当时我们是分两派,一个文战部,一个刺刀见红。放学后,我们拿着水壶和小碗儿,去官路畔和车路上,给串联的红卫兵送水。他们也给我们发一些毛主席语录得小纸片儿。走到哪里,都要背老三篇、毛主席语录。那时候,我老三篇全都背过了。我还能背多条毛主席语录,还有毛主席诗词。
有一次,生产队上在外地工作的周金成回乡(那时外地工作的人回乡,娃娃们都去看,想吃发的糖)。当时,他说谁能背下条毛主席语录,就给发一本红皮毛主席语录和一枚纪念章。我当时就一口气背下多条。他立马给了我一本儿语录和纪念章,我高兴极了。当时是潮流,手捧主席语录,胸前佩戴一枚纪念章,是一个标配,别的人都没有。一般人只是戴着用红漆刷的铁皮上面写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牌牌。每天晚上去这个村,那个沟,还有镇上,县上到处去看电影。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村里有两派,一个临委,一个联总。临委势力大,住在两岭村小学,号称是前哨指挥部。有一晚上,棣花猛虎队0多人来攻打小学,他们用梯子头顶玉米杆进攻。但是临委的人有着优势,举高临下,冲锋号一吹,整摞整摞的瓦、石头往下扔。他们冲锋了好多次都无法突破,他们被打得头破血流,0多人灰溜溜地逃跑了。那晚上,整夜号声冲天,瓦片石块,响声震天,给人们带来了恐惧,宁静的夜晚,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母亲整夜哎哎哎的叫唤,让人很是心疼呢。
那时候,晚上经常跑得去撵场子看戏,白天我们一伙儿,十几个人,记得应该是中伏天,每人背个背笼,拿着锄头、水壶,浩浩荡荡地出发去大峪沟挖药材。上东沟串西沟,上大寨顶,闯虎山老虎沟,天子平顶、腿畔沟、银洞沟、长沟、刀背梁、蛇蛛梁、八里石、拴马桩等。几十条沟汇聚在一起的山顶上,到处流落着我们的汗水和脚印儿。一般药材的品种有苍术、桔梗、沙参、天冬、穿地龙、玉竹、麦冬、八月炸等。我们都学会了分辨这些药材。有一次,在八里石岩上发现了大片的八月炸,那是我们挖得最多的一次。当时卖了20元,相当于现在的几百元呢。有一次,我们刚上到坡顶,突然狂风大作,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倾盆大雨,顿时我们是又怕又吓,坡上又滑,也害怕触电,连爬带滚就下坡了。每次,挖药回来还得收拾一下,用火烧,用刀子削。有的还得蒸,晒干后送到药铺,当时收药是一个叫老陈的老头儿,他要放称台上称一称,他手一敲,头一摇,账就算出来了。卖完药,我们就一块儿去饭店吃一碗大杂烩,0.3元一碗,或是吃一碗臊子面,才0.25元一碗。吃完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我一生爱劳动,在小学时,我就攒了多块钱。
还有一次,我和榜娃去大峪沟接大人砍柴回来。我们背着背笼,走到河滩,拾了一匣子火柴,拿上,边走边玩。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马拉沟对面的刀背梁。当时刮着风,抬头见坡上长满了柴草,也没想后果,掏出火柴。刚一点着,火就顺风势凶猛的扑上了山顶,四处蔓延,吓得我俩扑打了一会儿,汗流浃背,无济于事。对面人家的人,出来又喊又骂。刚好,榜娃他父亲来了。边闪着担子,边喊边骂到:“日你妈的!放回走,让你妈给你拿被子,往法院里走。”吓得我俩腿直发抖。还好,火快到山顶时再不往上着了,那边儿有树林,这边儿着到几里的地方。阴死崖下,没有草,火也就灭了。那一次,也算是给我们了一次教训。
7
年,我也考上了商镇中学念高中,当时都是推荐上学,只有72年考了一年,当时我成份高,加之读书无用类等言论,我没有好好学,我们班58名学生,考上了我们18人。当工人参军、上大学等都是推荐贫下中农,我也觉得读书无用,一天只上几堂课,就跑回家挣工分儿了。
我一生一直爱出力劳动,全队上就我的工分高,一般人都是一个月30到40个工分。而我,一个月老是多个工分儿,加班儿割草,背麦糠。晚上,通夜加班儿用打麦机打麦。每天挣三四个工呢。当时,我家是全队上第一个最大的余粮户。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我,都是主要劳力,两个妹妹还小,但放学后帮忙干活儿,基本上一家子都是劳动力,所以,一家人都是在父亲的带动下,勤劳吃苦。父亲就是我们的榜样。他一生从不求人,教育子女方面非常严格,不准抽烟,不准留长头发,所以我们一家人一直到现在,几代人都不抽烟,不喝酒,不偷不赌,没一个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事。可以说,都是热爱国家,热爱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由于勤劳吃苦,我们家的生活一直比较超前,当时所有人生活还比较艰苦,吃蒸红薯、酸菜黑馍、吃稻糠、红薯蔓子、柿子拌的炒面等。割柴割草的人都拿的是红薯、玉米面馍等作为干粮。我们去竹叶沟、阴死沟、茅房岩等几十里的深山沟砍柴担着回来。去时,一般都凌晨四五点了。冬天,天又冻又冷。脚穿草鞋,十几个甚至20多个人,冒着严寒,雄赳赳气昂昂,就像打仗一样,过完木桥,一次又一次地跳过几十次列石,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水里。当担着多斤柴返回几十里地,路上渴了,在阴死岩下,坡根下有一个小石坑,据说,多年来一直流淌着一股浸水,甘冽清甜可口。过往行人,到这里了,所有人都会歇一下,放下柴担子,把带的干粮泡在水里,边吃边喝。那么冷的冬天,但是大家又谝又笑,也不觉得冷,吃完后又继续前进,回来后,有的肩膀被磨烂,脚底打了泡,血都流了出来。第二天又继续去。可想而知,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的艰苦,多少次,割柴割草,手背被刀砍破,就浇上一泡尿来止血。因为,那时没有创可贴,让伤口自行愈合,然后继续砍柴割草。割草比砍柴要近得多。所以,我们一般都要担斤到斤。回来后,还要加班儿背麦糠,晚上整夜的加班儿,用打麦机打麦子。
(作者手稿)
在高中的时候,我也爱交朋友,基本上班里50多名同学和我都很要好,时不时地在一起逛街道,去丹凤县城看电影《卖花姑娘》《青松岭》《赵四海》《柳暗花明》等。
有一次,我请假去留仙坪拉柴。由于拉得太重,所以在下鱼岭水库的陡坡的时候,由于坡陡弯急,我很快扛不住车子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灵机一动,就把车子拐进一尺高的麦地里去了,由于车子失去了平衡,就爆胎了。当时,天黑了,也没有修车的,同伙儿带信到学校。正值晚上晚自习,同学们听了这个消息,一下子去了20几个人。你推我拉,说说笑笑地就把车子拉回了家。
那个年代,村上大会小会不断,也经常全县的公社大队,扛着各种彩旗,扭着秧歌,敲锣打鼓,放鞭炮,人山人海,去县里开大会,九大更为隆重,还有粉碎四人帮等活动。
年,我们就高中毕业了,毕业后就正式成了劳动力。回大队不久,队上让我当副业股长。我负责窑上的一切事务,烧窑、出窑、卖瓦。去商县熊耳山大荆煤矿拉煤。那时,车很难找,有时我找不下车,就叫拖拉机去拉。不行,就去大峪沟买柴,还要去丹凤的各个地方联系买砖瓦的单位和个人。那时候只能是人用架子车,一车一车的往县城拉。当时的纸厂、县委、东小、花庙、西小等,都用的是我们窑上的砖瓦。记得那时候,拉一页砖是一分钱,一车拉页砖,是一元五角钱。重量大约就是到斤左右。每次去,我都要拉一车子去验货。一般人都是一天去一次两次,可我和周述鹏,一天老是三次,累的人脚疼、身子疼。当时我对工作极为负责,认真,以身作则,带头挖土晒土,经常步行去县里联系买主,从没有花过集体一分钱。
当时,两岭村是五个队,我们是第三队,是最大的一个队。我们当时人口是户,上工时前面儿的人都到岭上了,后面儿的人还在村口,人是一溜带串的。那时庄稼成熟了,晚上要看庄稼、看墒情,一晚上就要留两个人在地里,一夜睡到天明。饿了,就到地里面拔一个萝卜,拔个红薯,或者弄一个莲花白吃。直接用手擦一擦就吃了。晚上加班儿离不了我,我爱出力,爱劳动,干啥我都争着去做。修河堤时,我最爱抬石头。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换着抬大石头,我们打赌,我一个人抬,他们十几个人轮换着抬。那次我一下子就挣了几个工分。每次干活儿,大家都爱和我在一起。
年,我第一次去西安,当时坐的是一个便车去姐姐家。去西安觉得啥都新鲜,开车的熟人就把我领到大雁塔、新凤公园、革命公园、动物园浪荡,又去了西安市武装部长家送了一付案板。吃饭的时候人家说,蒋介石死了,是内部消息。他还领我去北门大寨饭馆吃饭,第一次吃排骨,心里想,咋买的骨头让人吃,他给我夹了一个,我一吃觉得非常好吃呢。总之,第一次出远门儿,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到处都是马车、兜兜车代替现在的出租车,车水马龙,那时车很少,就是电车和公共汽车多一点儿。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回来以后,上工时,大家都问这问那,问我到西安的所见所闻。
8
我在乡村生活时,救过三次人。第一次,是在窑上干活时,听到说村里周述贤邻居的女儿从崖上掉下去了,我一听马上跑到出事的地方,当时把娃掉到一个大石头旁,满身是血,我就背着她,很快的跑上了车路,医院,后来娃好了,他家还拿礼物给道谢。
第二次,还是一个小男孩儿,当时全公社都在修马鞍岭,改河道工程,刚开始通水,因下雨水很大,河里搭一个独木桥。大家过去都要小心,当时我正在推着一车土,突然听到有小孩儿喊救命,一看一个小男孩儿两只手,扒着板桥,吊在空中,下面的水流得非常急,我立即放下车子,冲到水中,一手抱小孩儿,一手扶木桥。当我出水面时,觉得腿非常疼,这时候一看,鲜血直流,当时水下到处都是修河堤的放炮石,扎伤了腿。上岸后,大人也来了,我医院包扎,一个多星期我都没能干活儿,也属于工伤,那受伤的娃是我外婆家房后面的人,他家长名叫巩书平。事后,他们一家也拿着礼物去我家道谢说破烦。
还有一次,河里涨了水,夏季我和李宽本、李建朝等几个人在河边玩水,游泳。忽然,看到一个人从上游,一浮一沉的漂浮了下来。我们几个看到以后立马游了过去,把他救上岸以后,人已经昏迷了。提着腿,摔了几下,过了一会儿,慢慢地,她醒了过来,当时我认出他是队里一个叫玉斗哥的未婚妻,我赶紧跑回家去叫了他,把她背回去了。
那时经常有危险的事情发生。再陡的坡、再高的树都会去上,再深的水都要去过。又有一次,在竹叶沟割柴,两丈多高,一个石壁,我从上面不小心滑了下去,摔得脚腿都烂了。自己爬起来一看,没事儿,又继续砍柴。还有一次去河里的窑门沟口猪地摘棉花。我到树上摘蛋柿,不小心掉下去了,还好没有大碍。又有一次,我上振邦哥家的平顶树上摘蛋柿,一下子树枝断了,我就往下掉,当时心里明白,一下子抓住下面的树枝,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还有一次,割草回来,下了很大的雨,河水涨得很大,有一人多深。当时,我担着多斤的草担子,往水里一下,草担子结果给飘了起来,我只能一手推着草担子,一手搏击水,危险极了,一沉一浮地前进着,好不容易游到岸边儿草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我使出全力,把它扛到了饲养室。
到了年后期,到年,那时修磨丈沟水库,引水到两岭村水渠,大队抽出一些强劳力。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当时按一个人几米,来完成工作任务。我每次都是最早完工,我的秉性是争强好胜,在艰巨的任务面前,都能提前完成任务。从滚峪沟的河里往小沟梁上担石头,担着担着,忽然听到中坪村大队广播里说伟大的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当时,我们几十个人全部感到很意外,不约而同地啊了一声,同时每个人都泪流满面,也停止了劳动,站在那里哭着听着。通水以后,干旱季节,白天黑夜都要灌溉,当时村干部是周治明。本来晚上浇水,让党员干部巡渠,但是每次都是让我去。修苗沟水库时,到了春节,还是让党员干部去。他还是叫我去了。一天补助二斤细粮,是1斤面1斤米,白天干活儿,晚上睡在帐篷里,大家玩儿着谝着。
当时是农业学大寨时期,不准搞家庭副业。记得有一次,我们七八个去涌峪沟拉柴,踏着冰雪,背着多斤的柴,一次又一次背到住的地方,也就是旅社。睡在当地人家的柴草楼上。第三天后就往回拉,一车子基本上都拉0多斤,回来后卖了30元钱,剩下的自己烧。结果大队上知道后,就把钱和柴都没收了。还说是破坏农业学大寨。
随着政策的宽松,有一次也就是腊月初八吃过腊八粥,第二天我们十个人一块儿准备去河南内乡县拉红薯片子。当时粮食不够吃,所以我们11个人,初九晚上开始出发,我现在还记得有我李军富、李容忍、李新忍、李宽诚、李振海、李宽本、李高兴、巩书盈等。当时,在我们队的窑上,一人拿了一个柴棍,把架子车一个套一个。一路下坡,车套车就像一条龙飞快地跑着,一路唱着,笑着,遇到紧急情况,大家口喊一二,马上用柴棍子扛到车底下刹车,一路浩浩荡荡到内乡县已是晚上。人家连夜把楼上的红薯片,拿下来过称,装满车子还买了一些粉条,房主给我们做了饭,白面掺杂红薯面,吃了后就出发了。连夜赶路,冷冬寒天,回来是上坡,拉得人浑身汗流浃背。累得大家睡在人家场地里的红薯蔓子里。有时候,干脆就睡到柏油路上。第二天起来冻得人膝盖疼。到了资峪沟,家里人骑车接来了,才松了一口气。
到了78、79年,我们村五个生产队分成了12个队,我们三队分成了四个队,当时大家选我当队长,我一生不爱当干部,但大家硬是让我当,我就干了。当时,抓地就是抓纸蛋,我手气很好,一下子抓了个一号就是稻旱地,每块儿都是第一块,第一块地也是最好的。也离家最近,不管干啥我都冲在前面,我一生没有自私自利,但我脾气不好,看不惯懒人和爱迟到的人,上工来太迟的就让回去,不好好干活的,有时候还会骂上一句。
后来,我想出去打工,就让父亲顶替我当队长。就这样,我和周榜娃、周中民去了西安灞桥电厂干活。打那以后,便开始了我长达36年的打工生涯。
(作者手稿)
:周中新,男,高中毕业,农民,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两岭村人。
《商洛棣花古镇乡土文化研究院》
总策划:王良
总指导:贾栽凹
顾问团:贾平凹孙见喜穆涛
韩鲁华鱼在洋李育善
主编:郭世斌
责编:王晓红雷卫东陈斌
陈仓本卢毅
编审:刘建国刘朝宏贺立
主管部门:商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单位:商洛棣花古镇文化研究院
灵感与墨香齐飞,妙文共青春一色,欢迎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