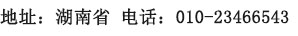1.
有个老头给了我五十万,让我回到年去。
2
也许是我经常咒骂那些神仙不给我机遇的缘故,总之那老头跟我说话的时候瞪大的眼睛差点没从眼轱辘里掉出来。他跟我说,如果钱用光了,我就必须回到原来的时代。也就是说只要有钱,我就能无缘无故地变老10来岁?感觉有点亏。
3
他遵守了诺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反正我回到了年,也许这就是神仙吧。
我站在一个垃圾桶边上,里面塞满了垃圾,甚至有不少垃圾落在了外边。望着远方低平的天际线,我想……这就是年,虽然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两岁的小屁孩。
老头很贴心地给了我这个时代的钱。我拿着一张百元大钞走进路边的报刊亭,拿了几张报纸,亭子的老板拿着钱左看右看,戴上眼镜又翻来覆去地看,反复确认后才把零钱找给我。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科菲·安南上任。年1月2号的报纸。回忆着这个名字,虽然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具体做了些什么就不清楚了。
想着这些有的没的,我走出报刊亭,一阵凛冽的寒风裹挟着沙尘打在我的脸上,些许硌人的沙砾钻进眼睛里。我“啊”的抱怨了一声,捂住眼睛,随后用手掌根部揉了起来。
“只要揉一揉,沙子就会随着眼泪流出来。”
脑海中响起某人的声音,一只柔软的小手用掌跟覆盖住我的眼眶,不知轻重地揉了几下,我害怕地哭了出来,随后睁开眼睛,沙子确实不在了。
虽然不知道这符不符合科学,但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
“说起来,她现在还在呢。”
8岁的时候,我的青梅竹马消失了,有人说她死了,不过我不相信。
我要去见见她。
4
来到儿时常去的供销社院场,在我记事时,供销社的院场已经成为了孩童们玩耍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宽阔的草坪,大家都喜欢到这里做游戏。
果不其然。走进开放的大门,放眼望去便是草坪,虽然现在看起来小了很多,但在当时可足够孩子们玩很多游戏。
今天的游乐场中只有一个人,一个披着头发的女孩,我想我认识她。
“你在干什么?”我走近问。
她在这深冬之际穿着一件棉絮外翻的小袄,脸上因受冻红扑扑的。她手中握着一把断掉的鸡毛掸子,同时小心翼翼地用枯黄的草绳去捆住掸子断掉的地方。
听到我的声音,她吓了一跳,慌忙抬头搜寻声音来源。在看到是一个不认识的叔叔后,她又重新着手修复工作。
“在修这个。”
“坏成这样了,还是买一个新的好。”
她把手上的东西朝身体移近。
“哪有钱。”
“我有啊,走,给你买。”
“真的吗!”她两眼放光,攥着木杆的手因用力而变红。
“嗯,叔叔很有钱。”
等等,总感觉很奇怪。我环视了四周,发现并没有人拿起手机报警,虽然这个年代有手机的人也不多。
“给我买!”
“噢,走。”
于是我们一前一后地朝大门外走去。期间她只是一个劲的低着头,摩擦手掌,呼出白气取暖。我们到达很近的百货商店,买了一把鸡毛掸子。
她拿着崭新的鸡毛掸子显得十分高兴,并没有跟我道谢就跑着回家了。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我叹了口气。
5
独生子女的日常生活就只能到小朋友多的供销社去,在那里的话总能找到乐子。当然,这都是在我家的小霸王购置之前的事情。
这样的地方难免会有各个年龄阶段的小孩,下到尚未上学,上到小学低年级。我们那时的玩伴都分了几个伙,一伙和一伙玩的游戏都不一样,年龄层也不一样,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最原始的歧视关系。玩卡片的看不起捉迷藏的,捉迷藏的看不起翻花绳的。如此这般。
而遗憾的,我那时就喜欢跟女孩子玩,因为其中两人住得比较近,所以更乐意和她们玩。于是我就被安上了“娘娘腔”这样的称号。虽然在当时并不觉得怎样,但终究还是看得懂空气中的恶意的。
不过,女生们的领头人可不一般,那是个敢和高一级的男孩打架的人,在她的庇护下,我这“娘娘腔”也能玩得很开心。虽然后来男生们总以各种名义来找茬,但都被这个“男人婆”给赶跑了。
不过这个男人婆却有着一般女孩子都没有的温柔。她帮我用“药草”包扎伤口,把我背回家里,一副大人模样地告诉我要当个好人。现在想想真是滑稽。
没错,这个“男人婆”就是之前见到的那个女孩。不过我并不知道她几岁,住哪里,甚至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6
年的五十万块是一笔大款,不过我是个不求上进,而且知识面相当狭窄的人。虽然知道这个年代两个马大资本家正在开始积蓄能量,准备一飞冲天。但我可没有到他们创业的地方找他们的心情,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到北京上海这些地方买些房子混吃等死。
不过……我现在是黑户吧,能买房子吗?真是麻烦。
将烦恼扫到一边,我离开住的地方,再次前往供销社。
女孩还在那里,孤零零的。
“在干什么呢?”我问。
“啊,叔叔……”她揪着枯黄的铁线草,有些惊讶地看着我。“上次的鸡毛掸子,妈妈突然生气了,揪着我去找百货店老板,问是不是我偷的。”
“啊……”听了她的话我迟疑了一会。这个年纪的女孩确实没能力买东西,是我武断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总生我的气。”
这个我也不知道。沉默了一会后,我问。
“你叫什么名字?”
“喜儿。”
“全名吗?”
“全名是韩喜儿。”
“几岁了?”
“7岁。”
原来如此。那么我5岁左右在这玩耍时,她已经10岁了。怪不得当时很多人都打不过她。
“叔叔叫什么?”
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我觉得不能说真名,于是胡编到:“王一二”。
“几岁了?”
“2…26。”
“和我妈妈一样大。”
“emmmmm.”听了这话,我的心中五味杂陈,甚至都展现到了脸上。
“叔叔脸真奇怪。”
“还不是怪你。”
“哈哈哈,人也很奇怪,明明大人都不会来找我说话的。”
她咧着嘴巴,笑嘻嘻地看着我说。
“你也很奇怪啊,怎么不跟小朋友们玩。”
“他们都去上学前班了。”
“那你怎么不去?”
“我家没钱……”
她垂下头,看着旧兮兮的胶底鞋鞋背。
看着她的背影,我拍了下她的背。
“任何时候都要坚强,不要垂头丧气的。走,叔叔给你买零食吃。”
“真的吗!”
“叔叔我最讨厌说谎话的大人了!”
等等……算了。
这次她走到了我身边,脸上洋溢着春日朝阳般的笑容。
“我弟弟快要出生了。”她说。
“弟弟?”
这个年代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二胎会被严格限制才对。
“嗯!到时候我要天天去给他买牛奶喝。我还要学织毛衣给他做衣服。”
“很厉害啊,姐姐。”
“嘿嘿。”
我思索自己的记忆,但是里面并没有关于她弟弟或者妹妹的部分。如果这不是平行世界,那么只有一种结果——
“你想吃什么?”我转移话题。
“泡泡糖!”
“泡泡糖有什么好吃的,不如吃巧克力。”
我和她走在马路边上,讨论着待会买什么。
“什么是巧克力?”
“额,一种糖。”
“那我还是喜欢泡泡糖,还可以吹泡泡,我可以吹很大的泡泡。嘿嘿。”
她炫耀着,比了一个大大的圈跟我说。
“那我可是能吹那————么大的泡泡。”我比了个更大的圈说。
“那我可以吹那——————————么大的泡泡。”她虽然想比一个更大的圈,但碍于手太短,没能做到。
“哈哈哈。”我们相视笑了起来。
突然,又一阵阴风吹过,沙石卷起打进了我的嘴巴里。我因为吃了一嘴苦涩的泥沙而露出扭曲的表情,本以为被看到后会引来大笑,但旁边却没什么反应。
“呜……”
她捂着眼睛,脸颊和脖子通红,似乎是沙子吹进了眼睛里。
“我帮你看看,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左边,是哪边?”
“额,你指给我是哪边。”
她指了指左眼,然后睁开右眼。没有进沙的右眼因为哭泣而变得微红。
我放下她捂着眼睛的手,用自己的右掌根部按在她的眼眶上。大大的手掌几乎盖住了她半张脸。
“只要揉一揉,沙子就会随着眼泪流出来。”
说着我揉了揉,过了一会,感受到液体浸湿手掌时,我才拿开自己的手。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我人生中第一次怀疑这个方法是不是有问题。
“治好了!谢谢叔叔!”
“不用谢。”
望着她有些委屈又有些高兴的表情,我仿佛看到了五岁时的自己。
“去买东西喽!”
“喂,等等,车路上不要跑!看车!”
7
年的初春我来到广州,当所持的钱转换成无与伦比的快乐与自信时,我甚至以为自己在做梦。高价值的钱可以买到任何我能看见的商品,这对于曾经长时间陷入名为贫穷的泥沼的我来说,简直是做梦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小时候……我甚至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父亲做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我只记得有一天我想吃一个巧克力,对父亲苦苦央求后换来的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虽说当时的我并没有多少金钱观念,认为所有家庭都一样有钱,但我着实不希望父亲以这种方式待我。
后来,为了偿还债务,父亲落入了“朋友”设下的圈套,不但没能翻盘,反而在赌局上借了高利贷,最终堕入深渊。
这样的绝望感传染到了我的神经上,一切看起来都是沉甸甸的,就连吸入的空气,都是潮湿而沉重的。
一次家暴后,家中一片狼藉。无法忍受他们大吼大叫的我,捂着耳朵逃离那栋房子,朝着高处,更高处,鲜有人迹的地方逃去,仿佛那里更让我感到温暖些。
站在一栋6层职工公寓楼的顶端,我俯瞰着潲雨过后还有些潮湿的地面。那一刻,我无比迫切地想要逃离这一切。
但是——她来了。
8
年的广州遭遇了房价缩水,一些地方的楼房甚至折半出售。虽然人们普遍抱着不能买房,否则还会跌的想法。但我很确信,未来这边的房子实在贵得吓人。不过……依旧很贵就是了,大概块一平米。
回到年的三个月后,我花掉了大部分钱,在广州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钱一下子就只剩十多万了。虽然房价还在跌,但我一点都不急。
但如果时间推进到年,房价就会翻一倍,卖出去后我手上就会有60多万,帮助父亲绰绰有余。
在广州享受了几个星期的早茶后,我又重新回到家乡。
重新去供销社的时间是周末,估摸着这天能见到喜儿,但与我想的相反,在那里并没有她的身影。
“你见到喜儿了吗?韩喜儿。”
我逮住了一个小胖子,这家伙未来会经常欺负我。似乎因为我是大人,他显得很老实。
“不,不知道。你们,谁知道啊!”
“昨天她妈妈生孩子,去医院了。她好像也去了。”
“医院啊?”
“镇上的卫生所。”
我点点头,谢了一声,然后离开了供销社。
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但我可没理由去看她妈生孩子。不过心中确实有一个疑问,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这个孩子应该生不下来才对。
以这个理由说服自己,我前往卫生所。虽然这个地方尽是不好的回忆,长大之后一次都没再进去过,但这次我还是勇敢地走了进去。
刚穿过大厅,就听见一个男人跟医护人员吵架的声音。内容大概是难产肯定是医生故意搞的,而医生们则解释说绝不可能。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