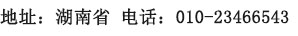1
母亲的娘家,位于她所读高中的南面。高中毕业后不久,她走过一条“L”形的乡间马路,嫁到了高中东侧的父亲家,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生为老幺的母亲,刚嫁过来时,屋里屋外,几乎什么活都不会。父亲与她一同生活,慢慢教会了她。生了三个孩子后,家里的负担重了,母亲跟着父亲早出晚归,外出扯草喂鱼。
生活的忙碌没有割断她读书时代的爱好。她依旧喜欢安静。当我们领着小伙伴们到家里玩闹,她总是一副无法承受的样子,“你们太吵了,房顶都快被你们的声音给掀掉了。”
闲下来的时候,她便看书,歪斜在床上看。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能读到的纸质书是很有限的。所有左邻右舍家能见到的印刷品,不论是名人名著、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还是《故事会》《知音》等,只要一被她发现,就会被“借”回家来。
母亲读什么书,我和姐姐就读什么,几乎没有半点选择。她喜欢猜谜语,有次在二伯家借到一本歇后语的书,她看了后,随后便来考我们:
“小葱拌豆腐——?”她考我们。
我们不知道。
“一清二白。”母亲得意地笑。
“给舅舅打灯笼——?”她又问,随后自答,“照旧(照舅)。”
猜歇后语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到了春季,正是插秧的时候。我生性毛躁,刚插进泥里的秧苗,前脚刚抬,后脚就浮上来了。这免不了招来一阵责备。但也有好玩的事。比如说,母女互猜歇后语的游戏,让机械运动的插秧,也不那么枯燥了。
人在划了格子的泥田里,插了一兜秧,便往后走。“脱了裤子放屁,你说后一句是什么?”为完成学校的好文好句摘抄任务,我将整本歇后语大全,一字不落抄了下来。到了这时,便可以来反问母亲了。
母亲答不上来。“多此一举。”我便得意了起来。母亲便将前句与后句念出来,嚼一嚼,琢磨琢磨,发觉果然是,便哈哈大笑起来。
这样几轮下来,我便有心记那些偏门的歇后语,只待第二天再插秧时,再去考问母亲,以此膨胀这份小小的虚荣心。
后来在班上,老师教那几个歇后语时,我很轻易就能对答,多半与母亲有关。后来喜欢思考,喜欢感受语言的精妙,多半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母亲喜欢在床上看书,但不允许我们这样。
她从外头借回来的武侠小说,看完一半被邻居喊出去有事,我们便算计好她回来的时间,把书拿到自己房间,倒床头就看。听到门外有动静,立马将书一合藏枕头下,果断装睡。母亲回来见了,明知我们是装睡,却并不多说。后来读大学流行一句“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便总是想起这一幕。
母亲读书只是闲读,“没什么事情可做,又不喜欢看电视,那就看书吧。”
我们读高中时,翻出没有封面的《红楼梦》在读,她冷不丁冒出一句,“《红楼梦》里的诗句,真的写得好。”
高中时,同学过生日喜欢互送书籍做礼物。我收到一本《三毛文集》,读完后,在二楼阳台上和姐姐分享心得。母亲在楼下听见了,“三毛真是个神奇的女子,在什么样的地方,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来。”
我们说,“这个人好的真好看。”“长得太漂亮了。”但母亲形容人长得好看,喜欢说,“长得真的是太美了,好美。”
我们说,天太黑了,“乌七八黑的。”母亲说,“是呀,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后来我们写作文,形容天黑得厉害,“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便条件反射般,窜到脑海里来了。
读高中时,母亲迷上了打牌。邵东一带习惯打字牌,大写和小写的字牌,从一到十,母亲俨然雀神,每天在家坐庄。打牌的爱好延续了很久,姐妹几个上大学后,她又爱好了看电视。夜里,这是她与父亲两人在家最惯常的消遣模式了。
前几年,母亲在几个朋友的邀请下,迷上了跳广场舞。一开始,总学不会,我们便连同她的舞伴,做她的思想工作,她便咬咬牙,坚持了下来。令我们姐妹几个佩服的是,她居然真的坚持下来了,越跳越好。
整个人瘦了下来,跳得一身轻盈。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好得很。很多时候,我们姐妹几个邀请她到我们所在的城市小住,她会这样拒绝,“这周末要学新的舞蹈,来不了。”遇见下雨或天寒的时候,学校的舞蹈队停跳,她便用手机或独立音响放广场舞的旋律,一个人在前坪跳。最初我们鼓励她,只是希望她能坚持锻炼身体。如今她多了一项爱好,乐于其中,这是我们姐妹几个始料不及的。
闲的时候,她仍然会读点闲书。放在书橱里的书,她会挑出喜欢读的小说来。像阿来的《尘埃落定》、吴念真的《这些人、那些事》等书,她就很爱读。碰上我们回家,她有时让我们推荐几本好看的小说,放在她的床头柜。
母亲现在读得少了,读书速度也越来越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凿”,她这样形容阅读的速度。
五一假后的第一周,父亲为了躲生,与母亲一同到湘潭过六十大寿了。他们歇了五天,回家那一天,正好遇上母亲节,在这前一天,逛天虹阅+书店时,看到周读系列有本名为《娘》的小书,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作者是彭学明。想都没想,买回来作母亲节礼物。
母亲半躺在沙发上读这本书。刚读一小页,她就不停赞叹:写得真好。我拿过来一看,书的第一段这样写道:“路的两边是田,田的两边是山。顺着田和山,娘背着我,进了寨子。”
尽管她杜德满,但不到半天的时间,她读完这本11万字的自传体纪实散文。读完后她说:“这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忏悔录。”
回老家邵东后,母亲把书留在了湘潭。
2
每个不懂事的孩子,多少会对母亲存有忏悔的情绪。就我而言,与母亲的关系,以十八岁为分界线。
“你的叛逆期,足足有十八年。”读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母亲突然这样对我说。我后来才晓得,母亲见到我的转变后,特意用责备的语气和我说了很多话,发现我仍然没有顶嘴,才这样说的。
我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叛逆期有十八年,但印象中,与母亲拌嘴的次数并不少。读大学时学心理学,提到家庭排行对孩子的性格影响,特别提到家庭排行老二的孩子,“性格叛逆、倔强”。我仿佛一下子就看见了自己。没有姐姐懂事,也没有妹妹乖巧,我总是在被责备。
母亲后来说,“费力的也是你,吃亏的也是你。”她举了例子。当时,嚷嚷要买什么吃的,姐妹中,我出面去说,遭批评的,自然是我。后来母亲还是给我们买了,但吃是三姐妹平分了。
远离了故乡与亲人,便开始会怀念。浓稠的乡情,将人裹得严严实实。从一个村庄走向乡镇,再走向县城及更大的城市,人一程程走远,也一程程孤单。
读大二时,很意外地收到了母亲的一封手写信。她在信里写道,让我多爱惜自己的身体,并特别提到,让我学会像尚雯婕那样坚强——我猜想她当时正在追看超女。我把那封信,夹在日记本里,心情低落时,便拿出来读,仿佛获得无穷慰藉。
母亲不会想到,那封信对扭转我们之间关系有多重要。爱的相互让留着共同血液的母女,一下子相通了。我开始打开自己的心,回到家,我们开始会卧聊至凌晨两三点,就如与闺蜜死党深夜卧聊一样。任何关系的转变,都不是单方面的。
年少时不懂事,会伤害母亲的心,不懂得换位思考用心呵护。懂得了换位思考后,开始更懂得了母亲,连同她的喜好与担忧。于是开始有了两种视角来看待母亲,一种是中立的,客观的,另一种,是带有温度与情感的。
人的观念变化,一些事便也会从尘封的记忆中浮现出来。读小学五年级,在学校里突发荨麻疹,几个同学送我回家。当时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家,她二话不说,背着我到隔壁村看一个有名的赤脚医生。发烧的我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地趴在母亲的背上。母亲背不动,走几步,便把我往上抛一下,以防止我跌落下来。
那是我记忆中,与母亲亲密接触的情景。读本科时有一次生病晕厥在路上,一个不知名的男生将我背到校医务室,我便立即感知到了儿时母亲后背散发出的那种气息。人在微弱的时候,有个后背可以依靠的感觉,始终让我迷恋。
因为思念,慢慢地会看见母亲的优点。
邻居家的婶婶,因为我家生了三个女儿,很瞧不起母亲,每每对母亲冷嘲热讽,母亲每每气得钻心痛,却又被父亲扯回家,不让争辩。后来我们都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常常回家。有一次,母亲特别嘱咐我,“你婶婶身体不好,也没人陪她去,你陪她去邵东看医生吧。”婶婶一辈子生性好强,母亲不计前嫌,这样的大度,是我没有的。这让我惊讶,也让我心里钦佩母亲。
相比之下,母亲不容易被人事所困,相信一切都顺其自然为妥。由此活得比一般人洒脱闲淡一些,很多时候,带有一股懵懂劲。
但我更认为母亲这是一种“大智若愚”。她与世无争,只求确切的闲淡幸福。在大事情上,她并不做主,但很多时候,轻轻浅浅一句话,却很有分量。我们姐妹几个,与世无争,多少与父母亲有关。
3
母亲的味道
母亲的爱,都融在了生活日常中,平凡又琐碎。我太愚钝,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对母亲来说,高中毕业后便嫁人,一直没有工作过,三个孩子,便是她唯一的事业,她的寄托与骄傲。
读初中时,天刚蒙蒙亮,她便要爬起来,给我们炒菜带到学校吃。读高中走通学,一日三餐,按时做饭,相当于陪读。三个孩子,每人三年。
姐妹们陆续读大学后,母亲便清闲了下来。每每回家,各种好吃的,便开始端上桌了。
母亲最擅长的,是蒸蛋饺。鸡蛋打碎,肉末剁碎,和葱段、盐一起搅拌。锅中放少许油,用汤匙舀一勺蛋汤放入锅中,蛋饼做成后,加入少许肉末,再用锅铲将蛋饼两边合上,蛋饺在锅里打个滚,压紧,蛋饺便做成了。之后,整盘蛋饺放入蒸锅,不出半小时,香喷喷的蛋饺便可以吃了。
邵东还有炖“年庚萝卜”的习惯,一大锅炖下,每餐吃饭,舀来一大碗热着吃。
今年中秋节回家,母亲备了满满一桌子菜。我们笑话她,问这些食材是哪儿来的。“萝卜菜是晚秀伯娘家的,草鱼和芋头,是二伯家的……”母亲不爱劳作,喜欢享受。但邻居们乐于与她打交道。因为母亲懂得反馈,并不会让人吃亏。
饭桌上,一些记忆就会浮现。一些植物或物品会突然将你召唤回儿时记忆中去,比如铁线烂草。
“给你一把钝感十足的镰刀,跟着我们出去,几乎什么草也割不回来。”妈妈为此说,“你们姊妹,以后跟着我们,真的是吃了不少苦。”母亲和父亲一样,后来不时会这样说。但我们姊妹几个,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一家人生活在一起,暖意融融的。这是父母亲带给我们的。
今天是母亲的生日,祝母亲大人健康幸福。
提子姑娘